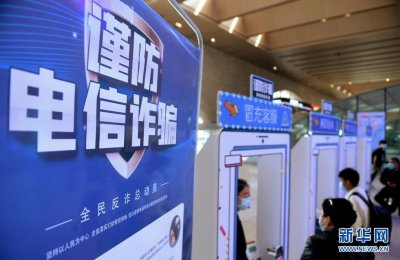南京杀妻富二代判死缓 杀害亲属恋人罪轻一等?
|
本网讯 南京杀妻案庭审现场。这一案件掀起新一轮情感纠纷杀人“罪轻一等”的争议。 图片来源:新华网 4月23日,笔者在本刊发表《“婚姻家庭纠纷”该成为“免死金牌”吗?》一文,从最新发生的南京杀害妻子的吉某被法院以“婚姻家庭纠纷”为由判处死缓说起,梳理了近些年一些发生在家庭成员以及恋人之间的案例,表达了对情感纠纷成为部分被告人“免死金牌”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的质疑,以及可能不利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担心。 这一话题并非新话题。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随着一起最新案件进入公众视野而被重新提起,争议一段时间后归于沉寂,直到下一个轮回。南京这起案件判决后,在网络上,对死缓判决也是有赞有弹。名为“@箱子鱼”的微博对判决做了善意理解:“我在想,是否法官从母亲已经没了,如果爸爸也没了,这个小娃就瞬间孤儿了的这个角度考量的?”而实名认证的作家“@沙欤”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凶手“并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却直接把‘婚姻家庭纠纷’当作了从轻的依据。这是个恶例,尽管不是首例。” 今天,笔者试着比较全面地梳理其中的法律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宏观层面对这一话题进行关注,无意也无力对个案判决是否适当作出评判。 “罪轻一等”:现实与例外 在《“婚姻家庭纠纷”该成为“免死金牌”吗?》一文中,笔者列举了一些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一是案件发生是罪犯丧心病狂的结果,被害人并无过错。比如,北京一中院判决的宋立明案,对被害人先掐脖子再用鼠标线勒最后用刀砍,仅仅因为“感觉女友对他冷淡”;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决的莫日来案,罪犯携带菜刀从海南赶到广州将前女友砍死,原因仅仅是对方违反“三个月内不能交新男朋友”的约定。第二个共同特点是,罪犯均被判处死缓。 2011年7月15日《南方周末》有关李昌奎案件的报道,佐证了杀害亲属可以得到相对轻缓判决的事实:“近年来,各地高院都有一些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命案,作出过死缓判决。比如子杀母、夫杀妻、弟弟杀哥哥等等。” 在李昌奎案中,被害人之一(另一被害人是其年仅3岁的弟弟)曾和李昌奎谈过恋爱。在二审由一审死刑改判死缓引发质疑之后,二审法院向社会解释改判理由时,也曾将这一关系作为改判的依据:“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来自上述《南方周末》报道)。
当然,并非每个杀害亲属的罪犯,都有被从轻发落的“幸运”。包括浙江杀妻科学家徐建平、杀害情妇的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在内,一些因情感纠纷杀人的罪犯被执行死刑。检察官杨涛在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了北京一个案例:2007年12月,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北京男子吴某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一审法院以“吴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且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及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为由,对吴某判处死缓。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北京高院认定抗诉有效,二审改判吴某死刑,并得到最高法院的核准执行(2011年7月22日《扬子晚报》)。 婚姻家庭矛盾引发杀人犯罪应十分慎重,确有明确规定。1999年10月,最高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2009年1月,在本报《人民检察》举行的“死刑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的界限如何把握”研讨会上,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周峰对于哪些属于民间矛盾以及为什么要对这类矛盾激化引发的杀人案区别对待,谈了个人看法。“我认为,民间矛盾的范围应该主要是指在普通老百姓之间,因为日常的生活、生产中的具体琐事所引发的矛盾纠纷,具体就包括了家庭亲属内部矛盾引发的纠纷,婚姻关系包括恋爱、感情纠纷,邻里摩擦……其特点是主要在熟人之间,对象是特定的,对陌生人一般不适用。而且作案人通常都是初犯、偶犯。从被告人的主观性来看,相对那些累犯、惯犯或者是暴力犯罪的主犯来说,相对对社会的危害要小一些。” 参加研讨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也对最高法院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认为,中国必须走限制乃至最终废止死刑的道路。“考虑到我国国情,我觉得首先从控制由民间矛盾引发凶杀案件的死刑适用率切入,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 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011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发布指导案例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二审均判处被告人死刑,最高法院未予核准,发回山东省高级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院最终改判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界定因情感纠纷杀人和社会上故意杀人在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方面的差别,通过区别对待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其必要性毋庸置疑。 执行中的偏差导致“同罪不同命” 减少乃至废除死刑是未来方向,梁根林教授所言是对的。但在立法保留死刑的现实下,少有被害人亲属愿意减少死刑的努力从自己亲人被害的案件开始。而以李昌奎案为代表的一些案件受到质疑,甚至需要通过再审改判的现实也表明,部分百姓对以此为突破口减少死刑的努力并不认可。 周峰对于因情感纠纷杀人行为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解释,大体说得通。但这个“小”是从总体而言的,也是相对的。具体到某些个案,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比其他杀人案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并不鲜见。所以,在2009年的研讨会上,他同时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对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是不是一律从轻处理,这恐怕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包括案件的起因,犯罪的情节,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被害人亲属的态度,社会影响,酌定量刑情节等综合考虑。对于那种虽然是民间矛盾引发的,但是如果是被害人没有过错,而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很卑劣、滥杀无辜的,即使是民间矛盾也不影响对他的量刑。” 应该说,他的这番理解,是对相关政策本意的准确解读。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实践中被机械理解。当倾向性的意见成为不考虑个案差别的“一律”,个案争议导致对政策本身的非议,便是迟早的事。2007年1月23日《天府早报》报道,某省高院明确要求全省法院系统,对于因婚姻、家庭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文提到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杀妻被告人由死缓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例。2008年1月22日本报报道过一起“相反”案例:农民杨立与父亲发生争吵,用茶杯、罐头瓶、砖块等物品击打父亲头部致死。法院一审判处杨立死刑,吉林省白城市检察院认为,这一案件是因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和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有区别,判决量刑畸重,遂依法抗诉。吉林省高院二审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改判杨立死缓。
两起案件案情不尽相同,改判在法律上都应没问题。我想通过它们的对比说明,面对同样的情感纠纷杀人,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司法人员却作出不同的判断——当这种判断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候,怎样的判断更理性更符合法律,便是必须追问的问题。 对于周峰有关因情感纠纷而杀人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解释,笔者上文的判断是“大体说得通”。之所以是“大体”而不是“完全”,是因为他讲的原因中包括这类犯罪发生在“熟人之间”。杀害熟人的危害性比杀害陌生人小吗?这是我的困惑。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也需要得到平等保护。以伤害对象是否熟人作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比较,本身就不应该。在我看来,“杀害熟人危害性较小”,是一个无法论证的伪命题。 情感纠纷引发的杀人为何要“另眼看待”?如果暂时理不出个头绪,我们不妨看看和它在同一文件中并列给出需“有所区别”的另一类案件:邻里纠纷杀人。杀一个邻居,和杀一个不是邻居的人,危害性有差别吗?很难说“有”。那么,为何要把它拎出来呢?因为此类纠纷发生,不少时候双方都有责任。如果被害人对于矛盾激化导致凶案发生有过错,对被告人量刑考虑相关因素,就是法律的要求。 情感纠纷杀人,也是同样道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些时候在情感问题上发生矛盾,责任很难完全归咎于一方。如果被害一方对于矛盾激化引发刑事案件有一定责任,那么,对于被告人“网开一面”,无论在情理上还是法律上,都并无不当。所以,对于情感类纠纷杀人,判断是否应对被告人从轻的根据,是也只能是:被害人有无过错。 被害人怎样的行为可视为其过错,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一些国家法律的规定,可供参考:《德国刑法典》规定是“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意大利刑法典》规定是“他人的非法行为”;《瑞士刑法典》认为是“非法刺激造成行为人愤怒或者痛苦”;在英国,陪审团发现证据证明被指控者是在被激怒情况下而失去自我控制时,应该考虑这种激怒是否足以使正常人也像被告人那样实施该行为。 用上述过错标准审视一些案件,我们常常困惑:不答应被告人求爱,被害人有过错吗?被怀疑有外遇而否认并辩解,被害人有过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杀害被害人的被告人“罪轻一等”的根据,究竟在哪里呢? 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通过区别对待正确适用法律减少死刑,对情感纠纷杀人“另眼看待”的初衷不错。但执行中的偏差,却削弱了这一政策的效果。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 第一,如何让这一政策发挥更好效果? 个人认为,关键是严格把握被害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的,被告人可以从轻;没有过错的,和其他案件“等量齐观”。 同时,应准确界定情感纠纷。比如,在我看来,向人求爱对方未答应引发的杀人,尚谈不上“情感纠纷”。这类犯罪,就不宜归入情感纠纷犯罪范畴。 第二,减少死刑的突破口在哪里? “从控制由民间矛盾引发凶杀案件的死刑适用率切入减少死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这是学者的解读。如果这确系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初衷之一,那么,这些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思路并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如果有人说“民众观念需要引导而不是迎合”,我不想抬杠,我想说的是:在情感纠纷引发杀人案件频发,一些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现实下,被害人亲属以及普通民众的感受,司法机关不能不察。将这类犯罪作为减少死刑的突破口的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应慎重考量。 第三,关于死缓制度。 从死刑到死缓,从死缓到死刑,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案件格外敏感,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法律后果“天壤之别”。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最终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为数极少。从法律后果看,死缓更接近无期徒刑。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只是执行方式不同”的解释,不免苍白。 死缓是我国独创的死刑执行方式。在建国之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为了实现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保存劳动力以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原则,中央决定,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凡应杀的,只杀引起群众愤恨的有其他严重罪行的有血债者,其余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死缓也适用其他应判处死刑而又不必立即执行的刑事犯。多年来,死缓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甚至为司法不公埋下隐患。2011年7月2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披露,死刑复核权的统一上收后产生一种不良现象,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死刑判决不被核准,主动减少死刑判决的适用,该判处死刑的不判死刑而降格成死缓。这样既能有效避开最高法院的“挑剔”,也能避免因为被“打回”而影响当地政绩。笔者判断,这样的情况应属个别,但足以引起警觉。 就目前看,死缓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还有多大?如果考量结果是仍有存在必要,那么,让二者界限相对清晰,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 村支书私吞8万元买车 法庭上称对不起政府培养 04-20
- 受害人遭殴打强奸 被签买卖合同保证“能生育” 11-18
- 侵犯商标权而变更企业名称的判例 11-08
- 逃犯化名进厂打工 投保后死亡获补偿 02-07
- 夫妻吸毒产生幻觉驾车冲撞小学校园 双双获刑 06-24
- 以打架为由开除员工,员工获违法解除赔偿金 01-10
- 职员诈骗银行要负民事赔偿责任 04-04
- 新疆伊犁新源破获200余公斤毒品案 涉案4人被刑拘 07-30
- 离职经济补偿 10-13
- 新疆哈密警方打掉一特大贩、吸毒团伙人员11人 07-30